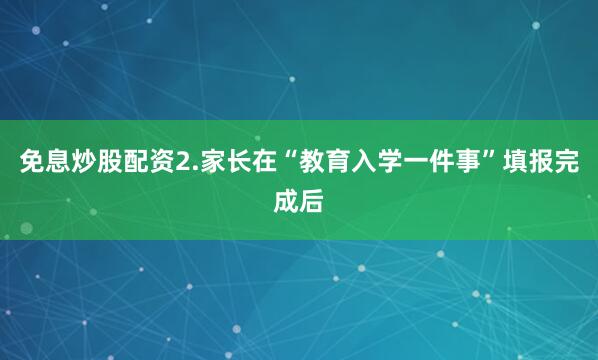1948年12月19日,老蒋给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写了一封亲笔信,这封信是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从南京带回陈官庄的。
杜聿明在《淮海战役始末》(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十一辑)中复述了那封信的主要内容:“(1)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,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,一再要求夜间突围,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。到十五日晚,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,毁灭了我们的军队。(2)弟部被围后,我已想尽办法,华北、华中、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,无法抽调,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,击破敌一方,实行突围,哪怕突出一半也好。(3)这次突围,决以空军全力掩护,并投掷毒气弹。如何投掷,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。”

老蒋这封信开头就骂黄维,最后又决定在内战中使用毒气弹,可见此人不但刻薄寡恩,而且凶狠毒辣——黄维对老蒋可谓“忠心耿耿”,直到特赦后也不肯写文章骂老蒋,还在1983年对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的王春景表示自己有“两个不骂”,其中一个就是蒋介石:“蒋对我个人来说,真是恩重如山,有知遇之恩。我原来的字是‘悟我’,是蒋将‘悟我’改作‘培我’,我理解,‘培我’,乃培养我也,恩人嘛,我怎么能随便骂他呢?(事见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《纵横》1999年第四期《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》)”
黄维是读书读得太多,以至于有些呆气,战败三十多年,已经当上全国政协常委、文史专员的黄维还在替自己战败找借口,他滔滔不绝地告诉王春景:“我的部队饥寒交迫,没有饭吃,吃草根剥树皮,把军用战马都杀掉吃了,而陈、粟的部队,虽然武器不如我的部队,但他们的士兵打仗勇敢,不怕死。特别是他们的部队有饭吃,几十万民工推着小车子给他们送馒头、稀饭吃。我的通讯副官是地下党,当时,我的行动命令一发出,解放军军就知道了,我的部队一举一动,解放军那里了如指掌,其原因就是我的通讯副官给共军报信儿。(这段话笔者进行了个别字句改动,因为黄维直到1983年,还没有改变对我军的称呼)”
难怪跟黄维平级的败将们会给黄维取那样一个绰号,他这个人有时候还真是脑筋不会转弯。

黄维带着第十二兵团去救黄百韬的第七兵团,结果黄百韬没救出来,黄维还把自己搭进去了。
可能有些人会弄混将军将领的名字,这也难怪,因为黄百韬又叫黄伯韬,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叫,这二黄一杨凑到一块儿,看着确实也有点乱。
黄维没救出黄百韬,还弄得第十二兵团全军覆没,杨伯涛想起来就生气,他在《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》中评价黄维:“很多干部曾做过黄维的部属,熟知黄维性情孤僻、严峻寡恩,一贯对之不满,这次又来领导,无不灰心丧气。特别因黄维久离部队,对反人民战争是一个外行,害怕断送在他手里。”
杨伯涛是黄埔七期、陆军大学第十四期,黄维是黄埔一期、陆军大学第一期,黄维1938年5月就接替罗卓英升任第十八军军长,而杨伯涛是1948年7月才当由整编十一师恢复的第十八军军长,据说黄维还不太承认杨伯涛是正式军长(按惯例,晋升军长后职务军衔基本都是中将,比如十二兵团另外三个军长、覃道善、熊绶春,但杨伯涛一直是少将)。

黄维不承认杨伯涛是真军长,杨伯涛则说黄维是个外行。黄维除了例行公事写了自己如何在淮海战败,还用了很大精力跟邱行湘、杨伯涛等人因为陈诚而打笔墨官司,在写军事史料方面,黄维显然不及杨伯涛——杨伯涛写的美军战术研究材料大受好评,并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,黄维则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。
杨伯涛比黄维早获新生十六年,但却一直没有原谅黄维。杨伯涛在《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》中很明确地表示,要不是黄维呆气十足且一意孤行,十二兵团就可能逃掉了。
1948年11月21日,黄维兵团司令部进驻南坪集,下属四个军(包括一开始没来的吴绍周八十五军)也都凑齐,同时解放军主力也开始合围过来,黄维乱了阵脚,居然问计于吴绍周和杨伯涛,杨伯涛建议:“趁东南面还未发现情况的时候,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,南坪集到固镇只八十多华里,一气就可赶到,一方面取得后方的补给,一方面和李延年兵团合股,再沿津浦线向北打。”
黄维带领的是机械化部队,八十里对他来说并不算是很远,但黄维犹豫不决:“黄维紧锁双眉,在房子里踱来踱去,焦急地考虑着。一直拖到半夜十二点,始决定兵团即刻向固镇转移。”

当时定好的逃跑方案是以熊绶春的第十四军沿浍河南岸占领阵地,向北警戒阻止解放军的南下,以掩护兵团的转移;以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以主力于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,向西北警戒,以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的转移;覃道善的第十军迅即脱离战斗(当时已经开打了),在吴、覃两军的掩护下沿浍河南岸向固镇奔逃;同样已经接火的杨伯涛第十八军也脱离战斗,跟快速纵队一起经双堆集向固镇西北湖沟前进。
读者诸君请注意双堆集这个地名——黄维就是因为行动迟缓,才被包围在双堆集,要是他早点行动,就一定能在解放军合围之前逃到固镇,这一仗我们就不好打了。
幸好黄维这个纸上军事家跟袁绍一样优柔寡断“见事迟”,这才拖住了第十二兵团逃跑的后腿,杨伯涛气愤地回忆:“我部署完毕后又到兵团部向黄维报告部队行动措施。黄这时神态万分焦急,对我说:‘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。’我吃惊地问黄维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决心。”
黄维之所以改变决心,是因为他一个给吴绍周送信的参谋“丢了”,为了等这一个参谋,全兵团都得原地不动。

当时蒋军的装备已经十分先进,步话机已经普及到团营一级,有线电话更是一直畅通,更何况研究撤退计划的时候吴绍周也参加了,只需要打个电话就行了,但黄维偏得郑重其事派参谋去送信,而且在参谋“丢失”后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,就这么干等着:“我在兵团部坐等,黄维既不叫退也不叫进,整个兵团部队整装待发。到正午十二时,南坪集到赵集公路的西侧,有少数解放军渗入,破坏通信,第十八军和第十军正面的解放军渐形活跃有逼近之势。我几次向黄请示行动,未得要领。黄维最后才下了决心,命令各军按计划开始行动,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。如果以早上五点钟开始行动算起,则耽误了十一个钟头之久,按急行军速度至少走了六十华里以上的路了。”
11月22日下午四时,也不知找没找到那个丢失的参谋,黄维终于下定决心开拔,早有准备的杨伯涛只用两个小时就跑到了双堆集,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——要是黄维不耽误那十一个小时,杨伯涛的第十八军机械化主力和快速纵队就已经可以进入固镇,那时候解放军再想把他们全包围起来就困难了——起码十八军是可以跑掉的。
因为“夜间行动不便”,黄维决定在双堆集宿营,全然不顾解放军已经冲到近前展开了攻击,于是第二天天亮黄维下令接着逃跑的时候,什么都晚了:吴绍周第八十五军遭受迎头痛击,一个团长被击毙,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浍河,迅速击溃了熊绶春的第十四军,溃兵还直接把覃道善第十军各师的阵地冲乱,解放军乘胜追击,迅速将夏建勣第一一四师的炮兵部队及辎重部队全部活捉:“第十二兵团经过这一天的严重混乱,寸步未移,解放军各路大军则潮涌般赶到战场,团团包围,黄维兵团已插翅难逃。”

战场上每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关乎胜败,就更别说足足十一个小时了,为一个走丢的参谋而在大兵压境的危急关头呆坐十一个小时,这事儿估计也就黄维能做得出来,难怪杨伯涛临终还在念叨“黄维是个外行”。
黄维或许是一个好军校教官,但纸上谈兵的赵括到了战场上,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当机立断:能打则打,打不过就跑,跑就得跑出一溜烟。
尽管杨伯涛急得头顶冒烟,黄维还是不紧不慢,丢不下一个参谋,也不放弃一夜安眠,于是他到了战犯管理所,就有大把时间睡觉了。
杨伯涛的愤怒可以理解,读者诸君也可以摆上沙盘和地图琢磨一下:如果黄维头一天不是徘徊了半夜,第二天又为等一个参谋而浪费十一个小时,他一口气跑到固镇跟李延年接上头,又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?
李延年在淮海战役中侥幸逃脱,杜聿明要不是为救黄维,可能也不会在逃跑途中停顿,“走丢”了一个小参谋,导致黄维兵团因行动迟缓被围歼,如果您是杨伯涛,又会如何评价黄维?
国汇策略-国汇策略官网-网络配资门户-配资网站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